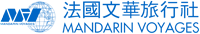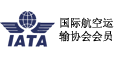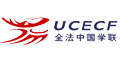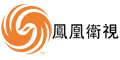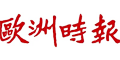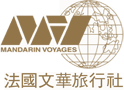说起巴黎,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塞纳河边的黄昏、铁塔下的野餐、还有街角飘着面包香的小咖啡馆。
但如果你搭上地铁1号线一路往西,大约二十分钟之后,巴黎突然就换了个画风。

摩天大楼、巨型雕塑、玻璃幕墙,还有一个长得像超大白盒子的“大拱门”。小编当时刚从站口出来的时候一下就懵了:我还在巴黎吗?
但别急着给它贴上“无聊办公区”的标签。其实,拉德芳斯背后藏着的是法国人曾经对未来城市的一次大胆想象——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实验。
一开始,他们真的想造一个理想城市
时间回到上世纪50年代。那时候的巴黎,老城区人口密度飙升,交通压力越来越大,市中心再一次“满员”。
像一个世纪前奥斯曼改造那样的大动干戈是不可能的了,只能继续向外扩。
于是城市规划者们就打起了巴黎西边一片丘陵地带的主意:干脆在这儿建一座新城区,一个现代化的、功能明确、容得下未来的城市。
 改造前的拉德芳斯,还是一片工厂区
改造前的拉德芳斯,还是一片工厂区
他们受到了一些“建筑圈大佬”的启发,比如勒·柯布西耶。这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提出过一个设想:城市应该高效有序,人住高楼里,路笔直通畅,地面只给人走,工作、生活、娱乐严格分区。听起来是不是挺合理?拉德芳斯就是在这种理念下诞生的。
所以你会看到,这片区跟巴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——没有古老的石板街道,也没有街角小面包店,只有高楼、广场、雕塑、玻璃幕墙,和成千上万的白领每天穿梭其间。

同时,严格的人车分流系统,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新区交通拥堵现象的发生,也让行人得以在宽阔的步道和广场间自由穿行。
 Louis-Ernest Barrias 创作的一组雕塑“La Défense de Paris”,纪念普法战争的巴黎围城战役,也是拉德芳斯名称的由来
Louis-Ernest Barrias 创作的一组雕塑“La Défense de Paris”,纪念普法战争的巴黎围城战役,也是拉德芳斯名称的由来
大拱门:现代巴黎的一声宣言
拉德芳斯最标志性的地标,就是那座巨大的“大拱门”(Grande Arche)。远远看上去像个巨型的白色立方体,其实它是对香榭丽舍大街尽头凯旋门的一种现代回应。

传统凯旋门是纪念战争与胜利,而大拱门要表达的则是“人道主义”——它不再纪念某个人或某场战争,而是向“人类”本身致敬。这种转变听起来有点抽象,但走近了你会发现,大拱门内部其实是个办公楼,上面还能登顶俯瞰巴黎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实用派象征”。
而且,站在凯旋门前,一眼望去,香街尽头就是这座大拱门,两者完美对齐——这是城市规划者精心设计的“历史轴线”,象征巴黎一步步迈向现代。
雕塑不仅是装饰,也是一种态度
拉德芳斯广场上最让人意外的,可能就是各种突然出现的巨大雕塑。比如:
卡尔德的《红色稳定体(Stabile Rouge)》,一个像被吹歪的大风车的红色巨构,热烈得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;

塞萨尔的《大拇指(Le Pouce)》完全按照真人拇指放大,纹理细节清晰可见:指甲、皱褶、甚至“指纹”都保留着。

阿迦姆的《La Fontaine Monumentale》,是一件街区级别的动态艺术杰作,即使当喷泉暂停时,水池本身的色彩与构造依然呈现出流动感,仿佛瀑布依旧在静静流淌。

...
这些公共艺术品不止是为了装饰,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:在这片被钢筋混凝土主宰的空间里,人类的想象力和艺术,是否还能留下痕迹?它们仿佛是理性都市中的“异类”,提醒我们:哪怕是最理性的城市,也需要一点感性和疯狂。
晚上的拉德芳斯:像极了“未来的空城”
白天的拉德芳斯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但晚上呢?下班高峰一过,整片区域会迅速变安静,甚至有点空旷得让人心里发凉。这就是这场“乌托邦实验”遇到的问题:城市建得很好,却没有生活的温度。

在“功能分区”的理念下,这里曾经几乎没有住宅,也缺乏夜生活——没有传统巴黎的街头文化,没有市民风浓厚的所谓“常驻居民”,没有夜晚的灯火人声。
不过,近年来,城市更新计划开始试图“补课”:新增住宅、绿色空间、餐厅和文化活动,节日季还有光影秀和圣诞集市。人们发现,乌托邦也需要“人间烟火气”。
 在Place de La Défense上举办的爵士音乐节
在Place de La Défense上举办的爵士音乐节
 拉德芳斯的圣诞集市
拉德芳斯的圣诞集市
乌托邦不是终点,而是一种可能性
拉德芳斯并不完美,它有时候看起来像个巨型办公园区,有时候像是建筑师的梦想游乐场。但它也确实是巴黎在尝试突破自我时的一次努力,是对“未来城市”最真实的实验室。
它并不是巴黎的“失败副本”,而是那个老巴黎试图与未来握手时留下的手印。
所以,也许乌托邦不是终点,而是一种持续修正、不断试错的过程。而这场实验,还没结束。